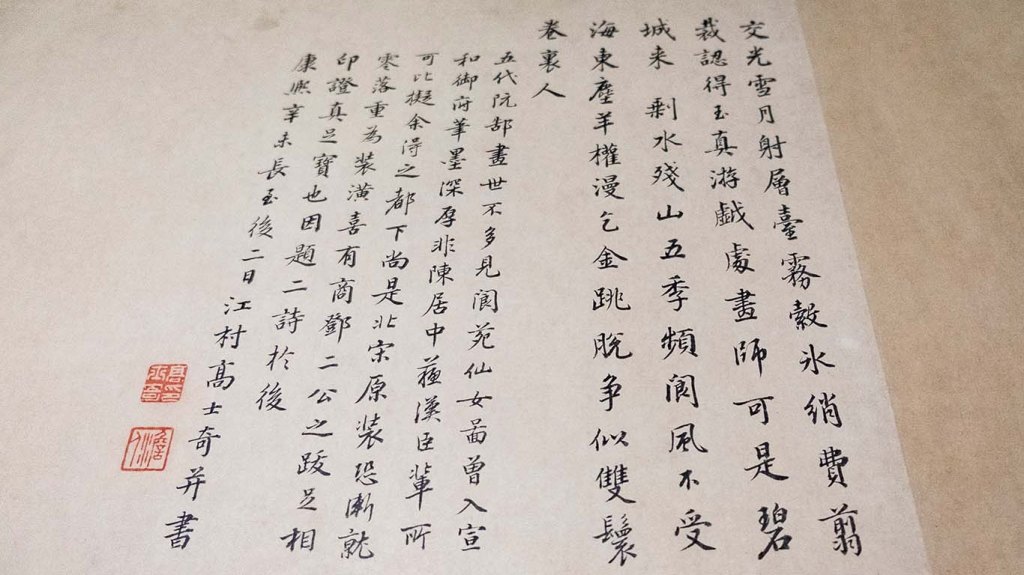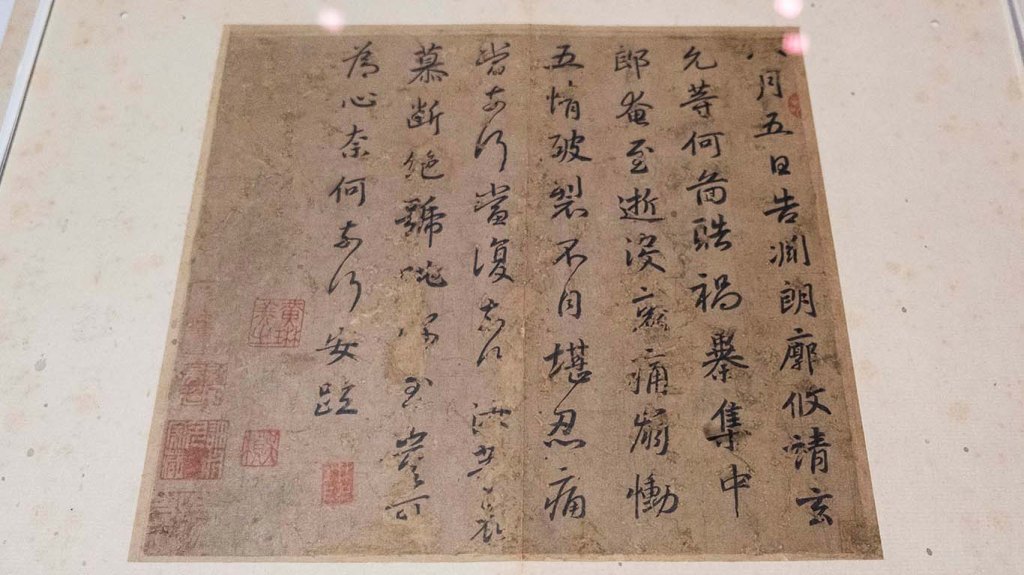博物館辦特別展覽,通常都會有一個特別題材,然後挑選相關藏品展出。題材或許是某個文明,也可以是某個時段,視乎外借藏品的一方有什麼可供選擇,也看策展方的財政預算有多少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就向英國國家美術館外借了五十二幅畫作,舉辦名為《從波提切利到梵高》的特展,顧名思義,就是四百餘年間西方各大名畫家都參與其中,每人一幅作品,沒有特別想表達的東西,展示的純屬是西方藝術的發展與轉變。
五十位畫家,雖都是藝術巨匠,但名氣有大有小,這次挑幾幅知名度較高的略作介紹。至於從中領悟到什麼,或是純屬看到各人風格的不同,就看各位悟性如何。

(Sandro Botticelli: 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, c.1500)
依照展覽名稱,自波提切利(Sandro Botticelli,1445-1510),說起。其人生平,早已在專題展覽中介紹,不再重複,這次參展的是《聖芝諾比烏斯的三個奇跡》(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,約1500)。聖芝諾比烏斯是佛羅倫斯的主教,傳說中他行過三個神跡,分別為畫作最左邊的為青年驅魔、中間讓溺死的幼兒復活、右邊讓盲人重見光明。

(Raphael: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, c.1510-1511)
在旁邊的,則是大名鼎鼎的拉斐爾(Raphael,1483-1520),作為文藝復興三巨匠之一,參展作品為《聖母子與施洗者約翰》(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the Infant Saint John the Baptist,約1510-1511),特點為題材和諧、色彩柔和,與波提切利的作品相比,就突顯出雖然兩者年代相近,但畫風極度不同。

(Caravaggio: Boy Bitten by a Lizard, c.1594-1595)
文藝復興年代之後,就來到巴洛克風格作品登場,大多擁有顯著的明暗對比。卡拉瓦喬(Caravaggio,1571-1610)的畫作《被蜥蜴咬傷的男孩》(Boy Bitten by a Lizard,約1594–1595),就明顯看到男孩面上的光影,以及因此而突顯的誇張表情,讓人感受得到被蜥蝪咬到手指時的痛楚。

(Rembrandt van Rijn: 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, 1669)
同為肖像畫,身處荷蘭黃金時代的林布蘭(Rembrandt van Rijn,1606-1669)則收歛得多,其《六十三歲的自畫像》(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63,1669),並沒有誇張的面部表情,而是用了厚塗法,即以濃稠的顏料繪製,表現面上與衣服的紋理效果。

(J.M.W. Turner: 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, before 1837)
展覽的最後一部份,由泰納(J.M.W. Turner,1775-1851)所繪的《赫洛與勒安得耳的離別》(The Parting of Hero and Leander—from the Greek of Musaeus,1837前)放於正中,這畫取材自希臘神話的一個悲劇故事,講述分居於達達尼爾海峽兩岸的一對情侶,每晚依靠女方燃起火把作指引,男方游渡海泳前來相會,結果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,火把因暴雨而熄滅,男方失去方向,最終遇溺身亡。
泰納被稱為「光之畫家」,尤其擅長光線與氣象的處理。在《赫洛與勒安得耳的離別》中,作為背景的月亮與雲海,就展示了泰納的功力,亦可看出與泰納最著名作品《被拖去解體的戰艦魯莽號》相同的風格。

(Claude Monet: Irises, c.1914-1917)
人潮大多集中在展覽的尾段,因為這裡擺放著三位近代著名畫家的作品,分別為莫內(Claude Monet,1840-1926)、梵高(Vincent van Gogh,1853-1890)與高更(Paul Gauguin,1848-1903),放在一起更能看出三人的差異。莫內參展的是《鳶尾花》(Irises,約1914-1917),以紫、藍、綠色構成,據說是因為莫內當時已受白內障影響,導致顏色出現偏差。

(Vincent van Gogh: 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, 1890)
至於梵高的作品,則是《長草地與蝴蝶》(Long Grass with Butterflies,1890),無論是顏色還是筆觸,都比莫內的作品來得鮮明。這是因為梵高的作畫技巧,如林布蘭一樣使用厚塗法,一筆一筆把顏料塗抹在畫布之上,其顏料之濃稠,甚至令畫作像浮雕一樣突起。

(Paul Gauguin: 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, 1890)
曾與梵高短暫共事的高更,展出畫作為《窗前果盤和啤酒杯》(Bowl of Fruit and Tankard before a Window,1890),與莫內、梵高相比,又是另一種風格。前兩者的畫作,顏色是混在一起的,景物之間沒有鮮明的分界,而高更則強調輪廓線,也把立體透視要素去除,使畫作變得平面。

(Sir Thomas Lawrence: 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, 1825)
看完這個展覽,感覺像是上了一課西方藝術史,展示了四百餘年的變化。且不說展出作品是否知名度最高的畫作,單是在一個展覽中集齊拉斐爾、堤香、林布蘭、塞尚、莫內、梵高等著名畫家,就已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大手筆。美中不足的,是空有闊度而深度不足,雖然著名畫家雲集,但說明解釋不多,需要參觀者自身擁有一定程度的美術史基礎,才能看出個所以然,否則就如展覽封面畫作,湯瑪斯.羅蘭士爵士(Sir Thomas Lawrence,1769-1830)所繪《查理斯.威廉.蘭姆頓肖像》(Portrait of Charles William Lambton,1825)的主角一樣,托著頭然後若有所思而已。